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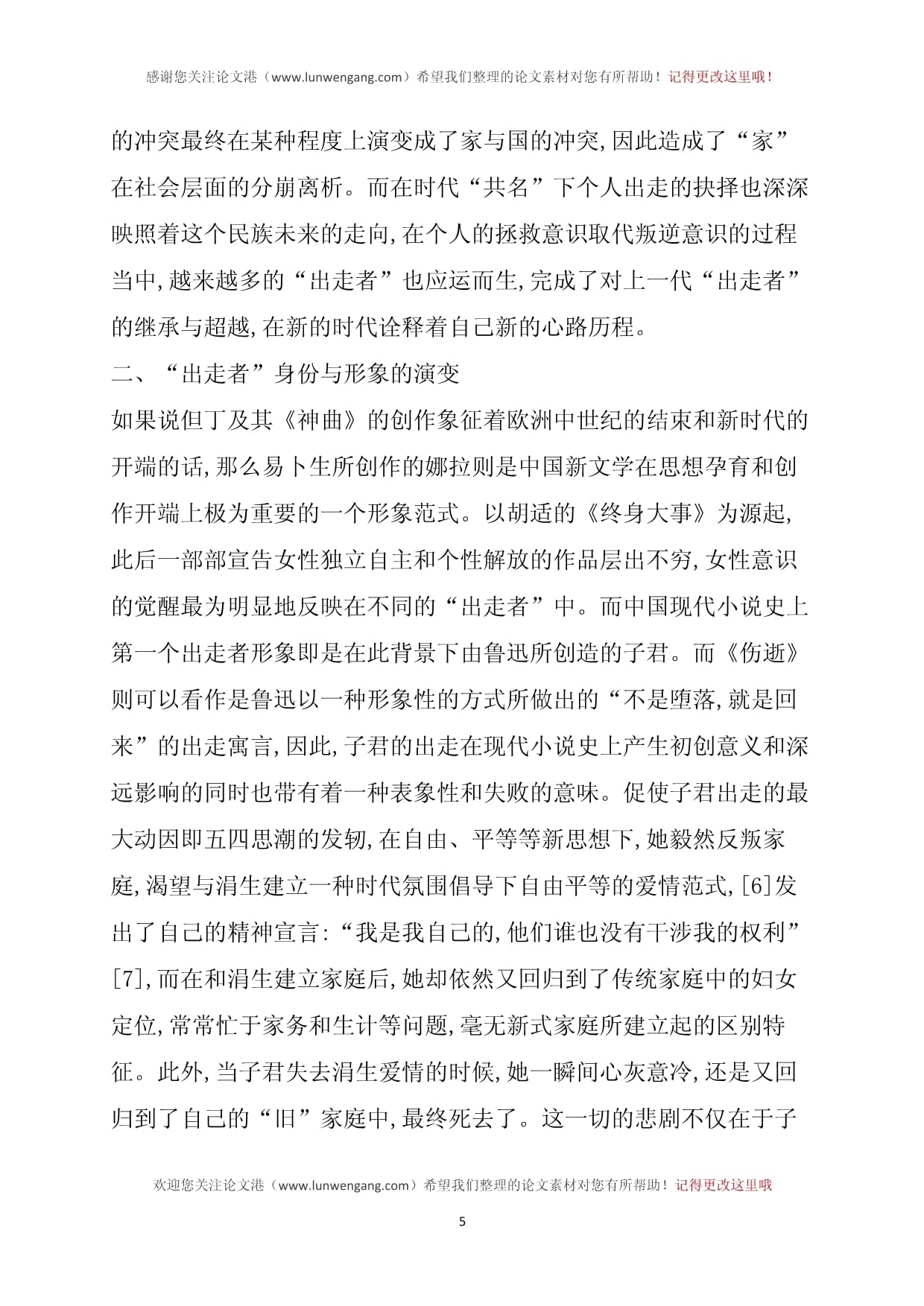
版權說明:本文檔由用戶提供并上傳,收益歸屬內容提供方,若內容存在侵權,請進行舉報或認領
文檔簡介
1、感謝您關注論文港( HYPERLINK )希望我們整理的論文素材對您有所幫助!記得更改這里哦!歡迎您關注論文港( HYPERLINK )希望我們整理的論文素材對您有所幫助!記得更改這里哦 我國現代小說中“出走者”身份與形象的演變摘要:在社會啟蒙占主導地位的五四語境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叛也自然成為重要的時代風向,而其中對于傳統的“家”文化的突破在當時受到大部分人的關注。新思想的覺醒和時代的突變促使人與“家”的沖突逐漸明晰,從而形成了個體對“家”的出走意識,“出走者”的形象也隨之產生和衍化,并從其發展中透視出了一種“出走”脈絡。但這并不能僅僅歸功于五四的啟蒙話語,其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發展有著
2、更為多樣復雜的闡釋。關鍵詞:“出走”;家;“出走者”;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May 4th,where social enlightenment dominates,rebellion agains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natur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of the times,and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traditionalhomecultur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ost people.The awakenin
3、g of new ideas and sudden changes in the times have gradually made the conflict between people andhomegradually,and thus formed the individuals consciousness of leaving home.There is arunawaycontext.But this cant be attributed to the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Its development
4、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40s has a more diverse and complex interpretation.Keyword:runaway;home;runaway person;在一般文學史研究視域下,往往將“五四”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源,與西方以重新發掘古希臘文明,通過傳統形式來革新文學的手段相對的,中國則是通過主動割裂和否定傳統,從而構成新文學的生成機制。“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而如果要在文學中對“家”這一根深蒂固的傳統機制產生解構性作用,從而呼應“現代”的話,可以說只有小說能夠承載這份歷史的沉重。而在之前的研究當中,這個問題也被
5、當作一個文學母題,如薛晨明在“出走”與“歸來”的二元困境現代作家筆下的“娜拉出走”母題探析中將女性“出走”的模式歸結為一種歷史與性別的困境,1但同時也由于過分強調性別因素而略顯單薄;吳暉湘在其碩士論文家:坍塌的神話試論現代文學中傳統家族文化的沒落與解構中也對現代小說中的“出走”題材與“家”的關系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析。2但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呈現出的大多僅僅是以羅列和梳理的方式來進行的單調概述,也僅僅是把“出走”作為認識論來研究,而沒有能夠將其提高到一個本體論的理論高度,并且還忽略了“出走”小說在現代小說史中貌離神合的發展脈絡和衍生譜系,尤其是在“出走者”形象的演變歷程中所顯現出的繼承與發展的
6、關系。他們不是獨立的個體,更多的是風云突變的中國現代史中,在強烈精神與物質壓抑下,與“家”這一碩大傳統文化體系進行博弈的人的精神寫照。他們是隨著歷史社會的變遷,一代一代散發和延續著新思想光輝的人,理應受到一種“史”的生命觀照。一、“出走”題材的源起對傳統家族的“出走”源于五四時代的作家們對其進行的社會、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疏離和排斥,這都使“家”在小說中更多的以他者的意義和身份出現,帶有一種陰冷黑暗的色彩氛圍,從而在文學中逐漸走向了歷史邊緣。但需要看到的是,短暫的時代激情在幾千年的“家”面前,自然會在不同程度上顯出其力量的孱弱,“家”正可以視作人類長期的心理積淀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體無意識的顯現
7、。正如榮格所指出的那樣,藝術品是一個“自主情結”,其創造過程并不完全受作者個人無意識的控制,它歸根結底不是反映作者個人無意識的內容,而是植根于超個人的、更為深邃的“集體無意識”。“家”對人的影響及其聯系可謂說是巨大的,因此,對家的“出走”除了出走者自身的覺醒和外部世界的感召以外,或許還需要一個重要的條件,即家族內部強大機制的自我瓦解。我國現代小說中“出走者”身份與形象的演變而在另一方面,造成人們大量出走的基本動因還是要歸結于個體自身叛逆意識的產生,而對“家”的叛逆即是承認傳統家族文化對人的壓抑,即主體心理生成了一個具有預設性的解構前提。3幾千年的傳統家族文化給現代人,尤其是受到過良好教育的知識
8、分子留下的往往是對于人性的壓抑,“家”的規則和傳統反反復復在吞噬著人的自然天性。如魯迅即在狂人日記中用極具現代主義色彩的手法發現和開掘了家族文化制度的不合理性,將封建家族禮教的幾千年的“輝煌”歷史濃縮成“吃人”二字,深刻揭示了“家”傳統對人的迫害。而“吃人”除了象征著個人人格精神的萎靡與畸形外,還表現為另外一種形態,即對人格循環往復的復制。如金鎖記中的長安,在曹七巧的壓抑和管控下,幾乎完全蛻變成了另一個新的七巧。“每逢她單叉著褲子,揸開了兩腿坐著,兩只手按在胯間露出的凳子上,歪著頭,下巴擱在心口上凄凄慘慘瞅住了對面的人說道:一家有一家的苦處呀,表嫂一家有一家的苦處!誰都說她是活脫脫的一個七巧。
9、”4隨著結局的到來,一切也都走向了沒落。可見,傳統的“家”在壓制人的個性自由時,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阻礙著家族自身新鮮血液的流動,5在陳腐的氣息一代又一代延續不更時,家族內部同時也發生著本體性的歷史解構,這就為“出走者”的誕生創造了條件。隨著五四的落潮,新思想的啟蒙及其所產生的叛逆意識對“出走”的影響逐漸減弱,但在風云跌宕的中國現代史上,任何一點社會性的時代突變,都有可能成為“出走者”們的反叛動因。從二三十年代革命政治激情的淡化到抗日戰爭的爆發,救亡壓倒一切,這時的“出走”已經不僅僅是對傳統家族話語的顛覆和個人自由的爭取,家對個人的控制以另一種方式封鎖著自身的開放彈性,阻礙著傳統的家國溝通,人與家
10、的沖突最終在某種程度上演變成了家與國的沖突,因此造成了“家”在社會層面的分崩離析。而在時代“共名”下個人出走的抉擇也深深映照著這個民族未來的走向,在個人的拯救意識取代叛逆意識的過程當中,越來越多的“出走者”也應運而生,完成了對上一代“出走者”的繼承與超越,在新的時代詮釋著自己新的心路歷程。二、“出走者”身份與形象的演變如果說但丁及其神曲的創作象征著歐洲中世紀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端的話,那么易卜生所創作的娜拉則是中國新文學在思想孕育和創作開端上極為重要的一個形象范式。以胡適的終身大事為源起,此后一部部宣告女性獨立自主和個性解放的作品層出不窮,女性意識的覺醒最為明顯地反映在不同的“出走者”中。而中國
11、現代小說史上第一個出走者形象即是在此背景下由魯迅所創造的子君。而傷逝則可以看作是魯迅以一種形象性的方式所做出的“不是墮落,就是回來”的出走寓言,因此,子君的出走在現代小說史上產生初創意義和深遠影響的同時也帶有著一種表象性和失敗的意味。促使子君出走的最大動因即五四思潮的發軔,在自由、平等等新思想下,她毅然反叛家庭,渴望與涓生建立一種時代氛圍倡導下自由平等的愛情范式,6發出了自己的精神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7,而在和涓生建立家庭后,她卻依然又回歸到了傳統家庭中的婦女定位,常常忙于家務和生計等問題,毫無新式家庭所建立起的區別特征。此外,當子君失去涓生愛情的時候,她一瞬間心灰
12、意冷,還是又回歸到了自己的“舊”家庭中,最終死去了。這一切的悲劇不僅在于子君失去了她所堅持和依靠的愛情,更重要的是,她至死都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結局。8可見,子君其實并沒有完全獨立,個性解放的新思想對她的影響僅僅流于表面,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她只是從一個“家”去到了另一個“家”而已。這其中除了社會條件的因素外,也有著人物自身的缺陷,子君們僅僅靠了外部思想表象的感召和一時的激情而出走,并沒有考慮出走以后,更沒有看到封建家庭傳統中所帶有的痼疾,這不能不說是帶有一些浪漫主義色彩的幼稚。不僅是傷逝,在五四時期眾多“出走者”的形象大多如此,這對當時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接受狀況是一個真實的反映,但這也不能不
13、說是很多題材初創時期很難避免的一種弊病。而之后“出走者”的發展則以家中高覺慧的誕生為象征,他具有強烈的批判和反抗意識,攜帶著極其進步的思維氣息。在封建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高公館,有著高老太爺的專制,頹廢萎靡的叔輩以及負載著沉重傳統枷鎖的大哥高覺新。巴金在談為什么要寫家時說:“我要寫包含在那里面的傾軋、斗爭和悲劇。我要寫一些可愛的年輕的生命怎樣在那里面受苦、掙扎、而終于不免滅亡。”9可以說,這時候的覺慧依然是五四熱潮啟蒙下的產兒,但五四僅僅是賦予了他一個如何看待家族和世界的思想,他的出走,更多的還是來自于在封建大家庭中身心受到壓抑而產生的靈魂困境,他看到了太多這個家族崩亡的前兆與這種死亡氣息對家中
14、人的迫害,如梅的抑郁不堪,瑞玨的悲劇遭遇,鳴鳳跳河自盡的悲慘場面等,都促使覺慧對這個“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訴”。覺慧是在新思想的吸引和舊傳統的凋敝的雙重契機下,他既受了思想的洗禮,又深刻地發現了家庭對人的戕害,這才決然“出走”,因此,這時覺慧的出走顯然比五四時期的子君們有著更為成熟和完整的姿態。在“啟蒙”話語以多種不同的形式延續和主導于文學中時,卻因戰爭的爆發而迅速被“救亡”所取代,同時,“出走者”的形象也在向更高的層面發生著演變。四世同堂一反以往的家族模式,沒有了傳統大家庭對人的精神殘害,更多的其實是一種其樂融融的家庭氛圍。但就是在這樣理想的家族環境和“救亡”的時代背景的沖突下,無形中限制
15、了人對更高維度的“家”國家的追尋,因此,祁瑞全的出走就具有了更為廣闊的社會意義,“他把中國幾千年來視為最神圣的家庭,只當作一種生活的關系。到國家在呼救的時候,沒有任何障礙能阻攔得住他應聲而至”。10實際上,老舍對于“出走”的態度是略顯曖昧的,正如他對傳統文化,尤其是北京的“家”文化,所顯現出的往往是一種“挽歌”式的姿態。老舍對瑞全的“出走”進行的是一種背影式的寫作,并沒有對他“出走”后著墨太多,更多的是對這個四世同堂的傳統家庭即將在戰亂中分崩離析的悲憫之情,并不像路翎在財主底兒女們中對蔣純祖離家后的生活經歷所進行的正面敘述。老舍對傳統家族文化進行理性反思的同時又伴隨著情感上對家族倫理的眷戀之情
16、,這就導致在小說中對“出走者”刻畫重心的偏移,但總體上來說,祁瑞全的出走很大程度上已經突破了五四啟蒙中個性解放的傳統,也從另一個角度刻畫了所不同于高公館的“家”,從家國關懷的人文理念出發,塑造了戰爭語境下全新一代的“出走者”形象,在繼承著以往“出走”的傳統中,也對同時期的“出走者”們開辟了另一種范式。同樣是宏大的戰爭背景下,在眾多的“出走者”形象中,也有著與其相異的身影。寒夜中曾樹生的“出走”即顯示出一種“新娜拉”的姿態。她與汪文宣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戀愛基礎之上的新式家庭,并且她的經濟能力遠強于丈夫,幾乎一人支撐起全部的家用,曾樹生從思想觀念和經濟的雙重意義上都在沖破著封建傳統以及“娜拉”出走
17、的五四傳統范式,也打破了魯迅所奠定的“娜拉”出走的結局定式,顯示著繼承又超越五四的一面。除了思想觀念的先導因素,促使其出走的另一原因同樣是來自家庭的束縛,丈夫的萎靡無能和婆媳關系的惡化,11很大程度上都使她感到孤獨與困頓,從而成為了現代小說史上最為果敢的“娜拉”。但同時,我們仍須看到,在曾樹生毅然出走的背影下,也蟄伏著矛盾和郁結。寒夜的發生顯然也是被置于戰時環境下,混亂殘酷的時代壓滅了曾樹生興辦教育的理想,在飛機的轟炸中,其超前現代的心理機制發生了轉向,她的內心還是有渴望安穩的那一面,希望有能干的丈夫作為自己的依靠,戰爭又喚起了她思想中固有的傳統傾向,傳統觀念與現代意識的沖突,在她的內心交替和
18、徘徊,構成了曾樹生這一最為飽滿的形象。此外,她對丈夫和兒子的感情也導致她在出走問題上一直猶豫不決,汪文宣的痛苦和疾病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戰爭造成的,混亂的社會現實一步步打擊著他的精神和肉體,而曾樹生正是由于對丈夫痛苦不堪狀態的憐憫,同時又不想為此消磨自己的青春和強烈的生命力,這才造成了她內心最為突出和強烈的矛盾。所以,可以說戰爭也間接導致了曾樹生的出走。以往“出走者”題材的小說多是描寫家的壓迫或者是外部世界的感召又或是二者結合,而忽略了他們出走時矛盾復雜的心理和情感,這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可以看作是巴金對以往寫作的超越,因為他注意到了曾樹生身上對“家”難以割舍的一份真情,強調了人與“家”的聯系是不
19、會那么輕易就斬斷的,在家庭束縛、戰爭壓迫和堅守個性的潛意識沖突下,曾樹生這一形象以及她的去留就表現出了小說史上眾多“出走者”形象前所未有的真實性、豐富性與深刻性。至此,人對“家”的“出走”姿態衍生到了最成熟的階段。三、結語現代小說史中的“出走者”盡管絡繹不絕,但究其出走的原因,大致可分為三類,首先是五四啟蒙下懷揣新思潮激情的人;其次是五四落潮后對家族和個體存在的思考中毅然掙脫封建傳統枷鎖的人;最后是在戰爭刺激下,對于家與“國”或者與個體存在尋求沖突有著強烈意識的人,他們共同在現代小說史上沖擊著幾千年以來一直延續的家族神話,用“出走”的方式宣告了“家”的坍塌。然而,傳統意義上的“家”在不同的作者
20、筆下,呈現出的卻往往是一種趨同性的模式。傳統的“家”大多都是對人造成壓迫或者阻礙著人的自由與理想,但這樣的現象是否帶有一種先入為主的主觀色彩,是值得商榷的。毋庸置疑,這誠然與很多作家的經歷都有著密切的聯系,如巴金的大哥之死等,“家”的確對個體的身心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但縱觀現代小說史中的“出走”題材,對“家”傳統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時代的要求顯然占據著高位,可以說,現代小說中對傳統家族文化的描寫已經達到了過度批判的性質,甚至不同程度上導致了這一文學題材的扁平化和單一化。在眾多的“出走”敘事中,真實而豐富的“家”卻淪為寫作的犧牲品,遭遇了遮蔽的命運。而這樣的敘事在四十年代的小說中才得以出現了不同的氣息和面貌。如果說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是通過正面描寫蔣少祖在其之后人生歷程的境遇來論證“家”對人的獨特吸引以及人們的重新認同,那么老舍則是寫出了老北京人幾千年來家族傳統文化基因的沉淀與真實形態,個體與家族的敘事沖突和思想矛盾進而才略微褪去了其對小說創作觀念先驗性的影響
溫馨提示
- 1. 本站所有資源如無特殊說明,都需要本地電腦安裝OFFICE2007和PDF閱讀器。圖紙軟件為CAD,CAXA,PROE,UG,SolidWorks等.壓縮文件請下載最新的WinRAR軟件解壓。
- 2. 本站的文檔不包含任何第三方提供的附件圖紙等,如果需要附件,請聯系上傳者。文件的所有權益歸上傳用戶所有。
- 3. 本站RAR壓縮包中若帶圖紙,網頁內容里面會有圖紙預覽,若沒有圖紙預覽就沒有圖紙。
- 4. 未經權益所有人同意不得將文件中的內容挪作商業或盈利用途。
- 5. 人人文庫網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僅對用戶上傳內容的表現方式做保護處理,對用戶上傳分享的文檔內容本身不做任何修改或編輯,并不能對任何下載內容負責。
- 6. 下載文件中如有侵權或不適當內容,請與我們聯系,我們立即糾正。
- 7. 本站不保證下載資源的準確性、安全性和完整性, 同時也不承擔用戶因使用這些下載資源對自己和他人造成任何形式的傷害或損失。
最新文檔
- 裝修施工合同模板
- 商業大廈租用與物業管理合同協議
- 煤炭倉儲合同模板
- 租賃合同管理與執行指南
- 石材采購框架合同
- 植物練習題(含參考答案)
- 合作研發合同樣本
- 房地產企業勞動合同簽訂指南
- 羊水栓塞管道的護理措施
- 標準民間借款合同模板大全
- 河南鄭州大學第二附屬醫院招聘考試真題2024
- (二模)溫州市2025屆高三第二次適應性考試數學試卷(含答案詳解)
- 7.2做中華人文精神的弘揚者 課件 -2024-2025學年統編版道德與法治七年級下冊
- 2025華電內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校園招聘筆試參考題庫附帶答案詳解
- 2025高考數學專項講義第18講圓錐曲線中的極點極線問題(高階拓展、競賽適用)(學生版+解析)
- 急性膽囊炎護理病例討論
- 15 青春之光(公開課一等獎創新教案)
- 社會主義政治建設
- 公共管理學方法論知到智慧樹章節測試課后答案2024年秋華南農業大學
- 2025年全球及中國居家康復服務行業頭部企業市場占有率及排名調研報告
- 苧麻生產碳足跡:基于區域、產物與經濟效益的綜合評價

評論
0/150
提交評論